
在千里達西班牙港的一場免費公開演講中,Lesley Lokko教授正在進行名為「熱帶滑稽」的講座;該活動由千里達與多巴哥建築師協會所舉辦。照片提供:Mark Raymond,經授權使用。
這是我們訪問Lesley Lokko教授的第三篇文章,亦為此系列最後一篇;Lesley Lokko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小說家、以及南非約翰尼斯堡大學建築研究所(GSA)所長。你可以於此處讀到第一、二篇訪問(英)。
由於擁有一半迦納及一半蘇格蘭的血統,Lesley Lokko教授在看待世界上有一套獨特方法。在迦納時,她由曾在英國接受教育的醫生父親陪伴長大,而17歲時,她前往英格蘭就讀寄宿學校。在那裡,她瞬間因為身為一名黑人--或準確點來說,因為不是白人,而成為一個「半階級」(迦納用來稱呼「混血兒」的用語)。
Lokko在此生都一直聰明地使用這個身在黑與白間的中間地帶,並用以孕育她的作品、她的建築師眼光,這樣的身份認同也影響了她的教學方式,以及在課堂中持續激盪出的文化及認同議題。
應千里達與多巴哥建築師協會以及該國最頂尖年度文學活動波卡斯文學嘉年華之邀,Lokko日前首次造訪這個雙子島國(指千里達與多巴哥,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就建築對今日社會的重要性、文學以及其他更多議題進行了幾場公開演講。
全球之聲(以下簡稱「GV」):你選擇在南非--這個地方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黑白關係的神經中樞--居住並追求你的教育職涯。身為一個處於後種族隔離的混血專業人士,你是如何與那個空間協調相處的呢?
Lesley Lokko(以下簡稱「LL」):部分南非白人,我必須要強調是部分,不是全部,讓我受不了的地方在於,我常感覺到我們的對話背後藏著一個訊息,那就是管理「改變」的這個責任應該落在我身上,因為我是想要改變的那個人。我們,也就是黑人,是那些想帶來改變的人,所以我們應該要處理後續--我把這叫做「歐普拉症候群」(Oprah Syndrome)。處理自己的情緒、自己所犯的罪的責任?他們並不想要,所以他們把這個責任丟回黑人身上。如果這不是種族主義,那什麼才是?我不是來這裡吸收你們的痛苦的。在兩百年來的歷史間,你們(指白人)已經談論了許多自身的痛苦了!我受夠了。
南非救助黑人政策(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簡稱:BEE)是南非政府透過為黑人公民提供白人公民所無法取得的經濟好處,來補救種族隔離所造成的不平等的計畫--這項計畫把進步與平等的論戰拉低到金錢的層面。事實上,種族問題並不僅僅與金錢有關。金錢是階級、文化、動能、啟迪、自尊、認同等議題的象徵,這些議題全都包裹在金錢之中。金錢成為最要緊的事,但它成了所追求的目的本身、而非用來追求更進步目的的手段。
GV:這就像是對於黑人認同的持續否認一樣。你在種族、文化以及認同上做了許多努力。舉例來說,對於我們這些融合多種族的加勒比人(另譯:加勒比亞人)來說,建築會如何影響我們的認同?
LL:因為非洲在歷史上即一直與其他地方,像是歐洲、美國、加勒比等地區建立關係,我們都深切地認知到「其他的」黑人文化……非裔美國人、西印度群島人、英國黑人等。我們感知到這些社群某種程度上與我們相連,但同時也是非常分散的--因此非裔人群的心理,無論我們在世界的那個地方,都是非常流動的。這與落地生根無關,不是說人只能屬於一個地方、只有一種認同、只說一種語言……這比那更為開放性。然而,這就是出現問題的地方:建築講的就是落地生根、地點、在這世界上的一個特定地區。身為建築師總有衝動想要去挖掘地基、在那裡放置些什麼、把它固定在地上,並盡可能確保它能屹立在那裡。所以,實際上,這門學科的本質總是與非裔人口離散的心靈本質有著強大的拉鋸--非裔人口的心靈本質是移動的、散佈的、多樣性的。
這對建築師而言是什麼意思呢?我會試著給你一個相當直接、而不是暗喻的例子:我有一名親近友人是多明尼加裔的建築師。她嫁給了一名瑞士建築師,兩人在瑞士巴賽爾(Basel)合開事務所。25年前,當她在康乃爾大學讀書時,還沒有關於種族或認同或流動性的討論。總之,她的事務所贏得了一個重建當地學校的案子,而在設計過程中,她決定要試圖讓各個教室有充足的光線,這讓她想起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光線— 柔軟、金黃色、薄霧般的光線。但巴賽爾的光線非常不同,更為冷調…是一種藍色、尖銳的光線。所以我的朋友帶了一小塊雅詩蘭黛的金色眼影到會議上與負責製作百葉窗的工程師開會;她說:「幫我做一扇金屬百葉窗,能夠把光線過濾成這個顏色。」然後他們做到了!這對她來說是個小小的勝利,因為這表示每當一個寒冷的冬日午後,這些百葉窗被拉上以後,教室裡的學生就沉浸於加勒比海的光線中,這是在巴賽爾長大的絕大多數學生未曾體驗過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特別是對那些非洲以及遠離故鄉的建築師來說更是如此;目前來看,他們正努力在把他們的情感回應、衝動及歷史融合於一個在歷史上將他們阻絕於外的學科中。
然而,我們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我剛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展覽中每個人都在問:「非洲在那裡?」沒有一個非洲國家參展,至少不是以國家的名義參展。南非政府租有威尼斯軍械庫(Arsenale di Venezia,為義大利威尼斯的歷史建築群,亦為雙年展會場)的其中一棟建築長達20年,但今年因為財政「不正常」,並沒有推出任何一名南非藝術家參展。於是那棟租來的場館就這樣空空如也。而回到南非國內,可以理解大眾對於政府讓這種事發生感到非常憤怒。這真的很悲傷。政府應該要提供機會讓文化發展……但南非政府並沒有這樣做。而所有非洲國家都是這樣。沒有一個非洲國家政府能夠提供任何一個非洲建築師去參與這場全世界最重要的建築盛會—-而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太窮負擔不起(而是政府並未提供相當的機會)。但目前的情況也同時反應了一個更複雜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公民與政府間的關係--我不認為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這兩造的關係會比在非洲更為嚴峻。
我們是一個深度封建的社會—-我這樣講並沒有「好」或「壞」的含義,只是陳述這樣一個事實。我常把非洲統治菁英階級的組成與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宮廷進行比較。一些部長級人物圍繞著一個強大的中心人物,仰賴他的恩惠過日子。但宮廷外的民眾活在21世紀,這個時代裡我們能夠取得大量資訊,得以見到其他地方、取得更多啟發、學習其他做事的方法……從福利制度到有效的公共服務等,然而,我們卻沒看到這些東西反應在我們領導人對我們的計畫或行動中。
事實上,一切幾乎完全相反。我們把政府視為某種能夠改善我們生活品質的慈愛父親角色,但是十有八九,這名父親角色注意的只有自己的口袋--還有他周圍人的口袋、而不是我們的。我們繼承的是一個時間上及空間上都來自非常不同根源的政治結構,我們很難適應。亨利八世之所以成為亨利八世不是為了賺錢;他已經夠有錢了。你可以質疑他是如何累積他的財富的,但事實仍舊是他有比四年政治任期久得多的時間來累積--而四年任期本身已創造出了壓力及誘惑。同樣地,你還是會看到擁有權力去改變現狀的政治領導人物,當中有許多是非洲人或非裔離散人口,例如曼德拉(Mandela)、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麥爾坎.X(Malcolm X)。
[ 影片:Lokko教授於安全空間系列#01上談論建築上的基進變革,影片來源:Vimeo UJ GSA。]
GV:加勒比海地區的領導風格也有非常類似的動能。
LL:我已經在建築研究所擔任所長四年了,每一天,我都不停地想著,領導地本身就像是一門職業、而不是你每天工作以外再去做的事,這就是你的工作。在企業世界中,有超乎你想像數量的資訊在談論如何去領導、如何去管理、如何創造更好的公司、更好的團隊……然而,在公部門,這種資訊沒有那麼多。我想,在企業世界中,它們的底線,也就是利潤,正是驅使它們成功的因素。
我檢視了許多政府單位裡的非洲領導者,我常懷疑他們當中是否有人曾擁有過領導所需的那種程度的協助。很有趣的是,我們從未談論這些支持機制,也就是領導者周圍的環境:心理面向、歷史緣由、指導方法--這些平庸的管理者與真正偉大的領導者之間的差異所在。
GV:你曾談論過你透過「把學生敲開」--也就是找出驅動他們的東西是什麼--的方式來進行教學。這樣做可能會有那些影響?
LL: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某一方面,我希望開啟關於種族及認同等艱難議題對話的影響能夠帶來巨大的不同,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發展到某一個時間段,這類問題不再被認為是邊緣性的、或不再只是為了黑人學生的利益而開啟的。
某種程度這是為什麼我在這裡(千里達與多巴哥)的原因。對我們來說(此處的我們,我是採用非常廣義的涵蓋範圍),重要的是擁有核心意義的空間及地點,像是真正頂尖的建築學校;這些空間在深度、正義、創造力、調查性、探索性上皆反映了其核心意義。這並非因為這些學生是黑人,你就「允許」這些黑人學生做的事。我想這是我在建築研究所身上看到的潛力。南非,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是將這些議題檯面化並成功達成目的的最適地點,那裡有足夠的基礎建設、足夠的教育經費;同時,這也是南非有史以來第一次,因為政治因素而勢在必行的議題。自從2016年的學生示威之後,每個人的嘴裡都在談「去殖民化」以及「轉型」。道德層面上的必要發展以及政治意志將會帶來改變。人們再也無法逃避這個問題了了。
GV:為了有效改變這件事,你在南非建築研究所採取了那些行動?你一定也曾得到了一些人的啟發。談談影響你的一些建築師及作家。
LL:對我來說,建築的開始以及終點都是在Mies van der Rohe身上。這是陳腔濫調,我知道,但這是真的。他的作品深深地觸動了我,我怎麼用言語也表達不出那種觸動。他的建築對我來說是「有道理的」,是受過七年特定形式現代主義訓練紮根於他身上後的產品。
文學則不太相同。我從未接受過文學訓練,所以我的品味可能會偏向於「直覺性的」,而非「訓練過的」。我在主題還有風格上都受到他人影響,我非常感謝我有受到過影響。有兩名作家對我特別重要--其中一位是南非作家Nadine Gordimer,我受她影響的地方不只有語言,這一方面的影響是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另一個影響我的方面則是她使用語言的方式就像是建築師使用空間的方式--她的語言具結構性、正式、非常陽剛。她是一個很難讀懂的作家,因為她並不遵循慣用的標點使用方式等等,但對我來說,她是最棒的。另一個影響我的作家是澳洲作家David Malouf。這兩人從廣義上來說都是後殖民作家,但是他們的作品正好示範了同一個主題可以被處理成截然不同的東西。至於西印度群島地區的作家,我在年輕人讀了很多Walcott和Naipaul。當代作家則有Patrick Chamoiseau和Junot Diaz。

Lesley Lokko教授在博卡斯文學嘉年華於千里達西班牙港的總部談論文學。Mark Raymond攝影,經授權使用。
GV:那麼非洲作家呢?
LL:我讀很多非洲作家時都遇到困難。他們有巨大的才能以及近乎無窮盡可講述的故事,但對許多人來說,他們是非裔的這件事仍舊主導著敘事。我已經等不及要擺脫我們書寫時常帶上的那層「他者」的連結或面紗…但這需要時間。
我即將與(與博卡斯文學嘉年華(Bocas Lit Fest)創辦人Marina Salandy-Brown)進行文學對談,主題是我在書寫第三本書以及第六本書後曾與我出版商進行的兩場談話。每一個人都跟我說,你的第二本小說會很困難,因為第一本表現得很好。但遇到困難的其實是第三本。我簽的合約要求一年寫出一本小說,但第三本花了三年的時間;拖到一個階段時,我的出版商真的受不了了,說:「把那女人帶到倫敦來。」所以我們到了倫敦,他們問我為什麼這麼難寫出這本小說。最後,我的其中一名編輯--她是個很好的人--對我說:「Lesley,看在上帝之愛的份上,我們不能理解你做不到的點在那裡。男人遇到女人,男人追到女人,男人失去女人,最後又再度追回這個女人。」我的經紀人,我想他應該為我感到非常抱歉,他向前傾對我輕聲說:「不要忘了,經典作品都是這樣寫的。」我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讓我感到比較不難過,但這句話確實讓我覺得自己沒這麼重要。但到了我的第六本小說時,我又回到同樣的會議室裡,進行一場非常奇怪的會議;這場會議成為我某場演講的主題:「拜託,三個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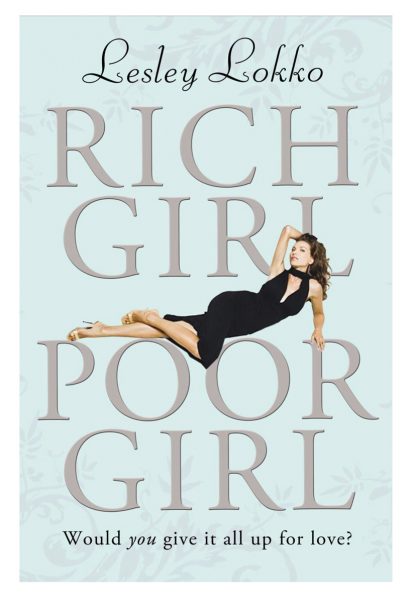
Lesley Lokko其中一本小說的封面。圖片由Lokko提供,經授權使用。
GV:「三個」什麼?
LL:(調皮地笑著說)我的編輯告訴我:「Lesley,我們剛才私下聊了一下,重點是,我們愛你的書……我的意思是我們只愛你的書」,然後我在想:「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然後她說:「但我們真的認為我們要畫下某條界線,所以我們剛才私下聊了一下、檢視了每一個細節,並且做出決定:我們希望你堅持三個就好,不要超過三個。」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我問他們:「什麼東西不要超過三個?你們可以說清楚一點嗎?」然後她說:「不要超過三名黑人角色。」
他們真正要說的是:「你看,我們尊重你認為你的每本小說中都要有個黑人角色,但你可以有點節制嗎?因為畢竟,你的讀者是在這裡。」這是讓我感到洩氣的其中一個時刻。這是一個行銷上的決策?一個道德上的決策?抑或是一個倫理上的決策呢?所以,我用我自己的那種諷刺方式回說:「混血算嗎?」最後,我不知道我是否算是遵守了這個準則,某些書裡的黑人角色比較少,某些書裡比較多;但對我來說,這是小說書寫階段終結的開始,因為我理解到,我認為自己在做的事與他人認為我在做的事其實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我認為我是在融合幾種不同的文類,包括言情、驚悚、純文學小說、歷史小說、政治回憶錄等等,但本質上來看,我只是在書寫BBC第五台「性與購物」風格的暢銷書,而這類作品總歸要遵循一套規則。所以雖然我認為我在扭轉規則,事實上我還是在遵從它們,就一個還是三個黑人角色在討價還價。我在寫了十一本小說後不再書寫,我的出版商和我友好地分道揚鑣了,但我仍舊認為他們低估了閱讀大眾。
對我來說,有趣的是,我的書在義大利仍舊非常暢銷,以我的整體讀者比例來說,那是我最大的市場。我的書在英國賣得更好,但是英國的讀者群本來就大得多。如果你看看義大利版本的書封,你會認為我是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作者,而且我在義大利進行演講時所被問到的問題是我在英國演說時從未被問過的。更重要的是,我的書中談論「黑人」議題的方式並不像整個文學世界討論這個議題時所採用的方式……我的英國編輯人很好,但是總是不太樂意以這些(黑人)議題作為書籍的主打重點、或是把我包裝成一個黑人作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會讓我被分類到書店中的黑人專區,最後只賣出三百本書--另外就是我不是那麼純的黑人。
如果你端詳Taiye Selasi 或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這些與我非常不同的黑人作家,他們就被包裝成黑人、或是非裔作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在文學小說的世界中(與商業小說世界非常不同),這樣的區別十分重要,而也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作品通常很直接並美麗地用一種當代的方式來直述與認同有關的議題。但像我這類的人就有點麻煩了,沒有那麼黑,也沒有那麼白,在寫作上也沒有特定文類,我認為出版商也很難處理這樣的人。
但英國公爵夫人梅根(Meghan Markle)的出現會改變這一切。我離開南非並開始這次演講之旅的一天,我觀看了英國王室婚禮--我感到非常震撼,原來我們在觀看一個具有如此深刻意義的事件,就算我們只是後見之明亦是如此。我想要針對這點再多延伸一些。如果有人問我我從那裡來,我總是回答:「迦納」。雖然我是由一名蘇格蘭母親在蘇格蘭所生的,我從不會回答「英國」或「蘇格蘭」--問一個混血的人他們從哪裡來總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無疑後續就會被問到「那你究竟是從那裡來的?」或是「那你的父母來自那裡?」如果有人逼問我,我可能會說:「嗯,我有一部分英國血統。」我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在英國讀書,那是個非常特別的時期。那時是酷不列顛尼亞運動(Cool Brittania)運動濫觴之時,這對於每個藝術相關領域的人來說尤其深刻。在那個時期,有某一個瞬間(我記得非常清楚)我突然意識到有英格蘭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以外的認同選擇--至少在白人本位主義的認同選擇之外。這種認同就是當代的「英國特質」--它給予這個前帝國的每一塊土地一種不同的、合法的意義,特別是在倫敦。對我來說,梅根的婚姻帶領大家走到了另一個方向,以一種其他人無法達到的方式,直入英國性的核心。我不知道它是否能立即改變任何事,但是,這是我記憶能及的第一次,「英國特質」被分裂了。
或許讓建築、文學以及其他形式文化表述所形成的現狀開始分裂會成為未來改變的動力。
校對:FangLing






